关注社会热点
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 观察家
在当前的语境下,保障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或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近日,一则邯郸三名初中学生杀害同班同学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目前,3名作案嫌疑人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另据家属介绍,尸检前,被害人父亲对孩子身体进行了查看,发现孩子头部、背部有明显伤痕。目前正在等待尸检鉴定结果。
不加惩罚无法达到预防效果
本案中,公众关切的第一个问题是杀害同学的三名未成年人因不满14岁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众所周知,刑法中有严格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而刑法理论也认为,未达到责任年龄的孩子因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对其予以刑事惩罚没有意义。
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此前,我国和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将14岁确定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限定。而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被认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对任何犯罪都不负刑事责任。
但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已经爆出多起不满14岁的孩子实施杀人等严重犯罪的案件。在此背景下,如果一律认为未成年人缺乏是非对错的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显然已与现实经验严重不符。
对于这些“恶魔”孩子,如果法律不加任何惩戒,不仅很难告慰被害人及其亲属,也无法起到预防效果。
因此,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借鉴了英美法系的恶意年龄补足制度,即其并未整体性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而只是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为一种例外性下调。
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同时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应当负刑事责任。
由于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如果构成重罪且情节极其恶劣的,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并送入未成年人管教所服刑。
而如果最高检没有核准追诉,案件就要退回行政系统,并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送到专门学校进行闭环管理。
留守儿童监护难题待解
事实上,此前已有大量的经验证明,很多犯罪的未成年孩子并非天生“恶魔”,其心理出现偏差并最终走向犯罪会经历一个过程。
在此过程中,如果有外界因素介入,在其价值观尚未确定之际,能够对其产生积极的引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早发现、早预防。
尤其是,要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强化对生命的敬畏。而不只是在学校教育中突出优绩管理,将教育异化为相互竞争的零和博弈和阶层突破的唯一路径。
换言之,将孩子培养成敬畏生命、尊重他人的个体,让其意识到自身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责任,而不只是将孩子作为学习的机器,将教育作为“成功”的跳板。如此,教育可能就更接近其应有的本质。
这起案件指向的另一个更令人痛心的问题是,留守儿童的监护难题。从媒体报道看,本案中的施害人和受害人无一例外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外出务工,这些留守儿童只能由老人隔代抚育。
但老人一般最多能确保孩子吃饱穿暖,不仅无法辅导其学业,也无法在孩子出现心理偏差时进行及时引导,哪怕是孩子遭遇长期霸凌时往往也难以觉察,更无法再进行疏导和帮助。
与父母一起生活,并在成年前接受父母的关爱,本应属于每个未成年人的权利。但因为一些原因,当前很难完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学问题,大量孩子因此长期处于和父母分离的状态。
我国留守儿童的数量相当庞大,长期以来,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离,难以接受父母的关爱和教导,各种违法犯罪问题也因此滋生。所以,本案也使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那些留守儿童。
用法律来惩戒那些施暴的孩子,甚至是让其父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许能起到改造和预防的效果。但法律的作用永远都是有限的。
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还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现有教育的缺失,如何确保孩子在成长时不会与父母被迫分离。
在当前的语境下,保障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或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方能在预防儿童犯罪方面做得更好,而非仅仅依赖于法律的惩戒。
□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初中生留守儿童法律校园霸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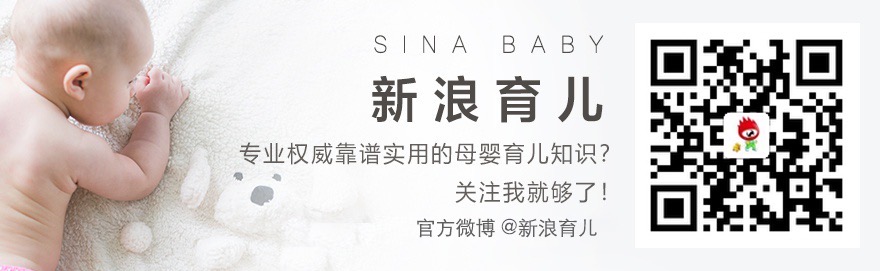 相关新闻加载中
相关新闻加载中上一篇 呼吸道感染期间能否接种疫苗?